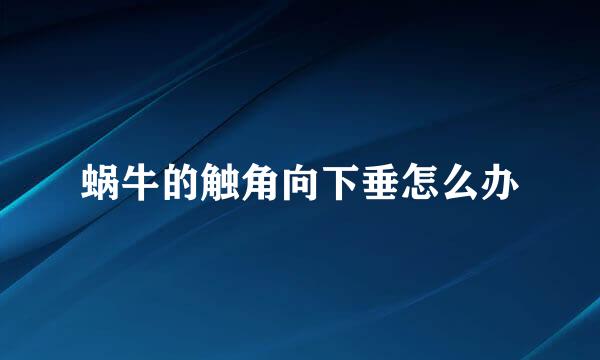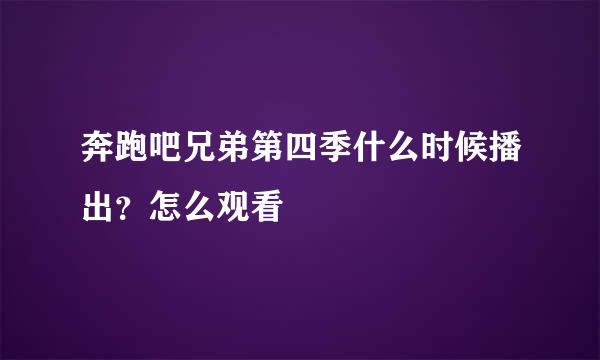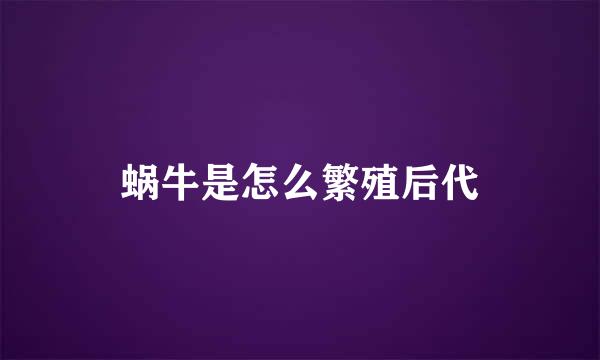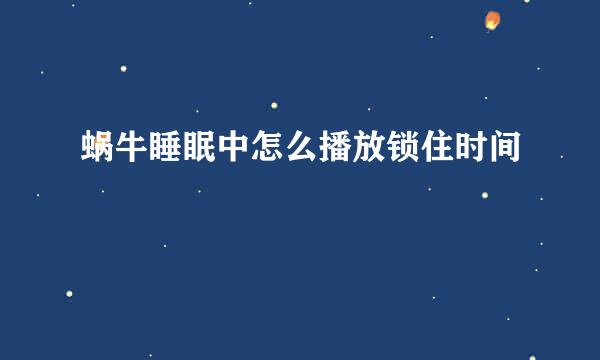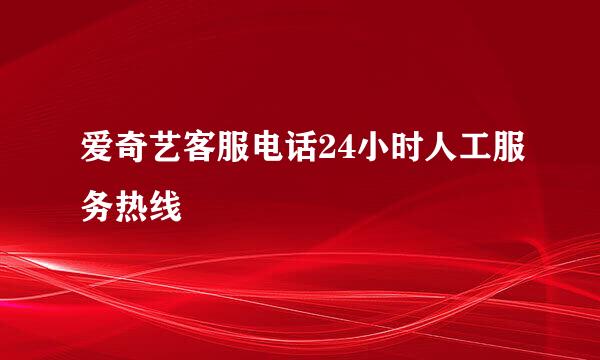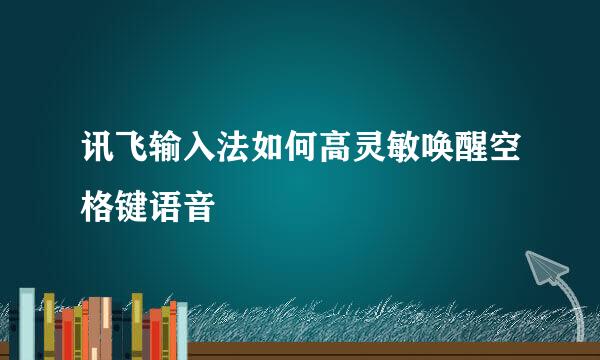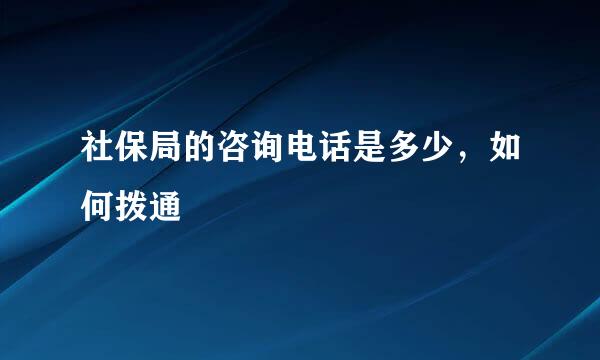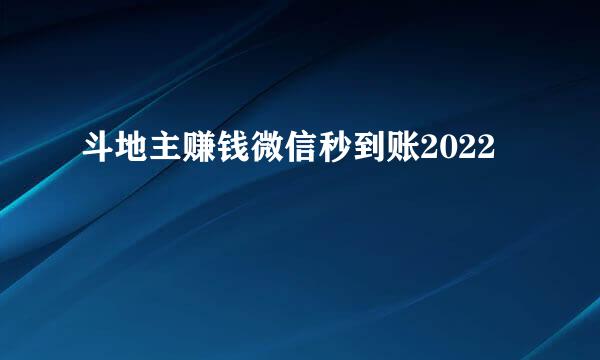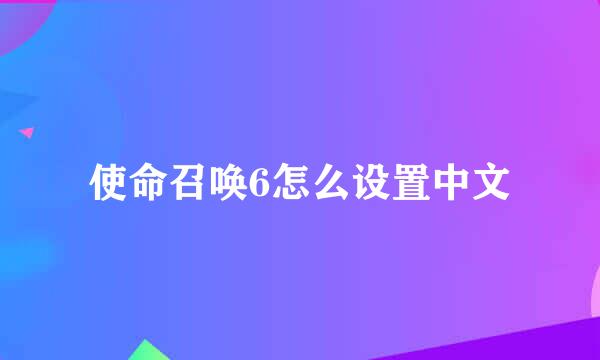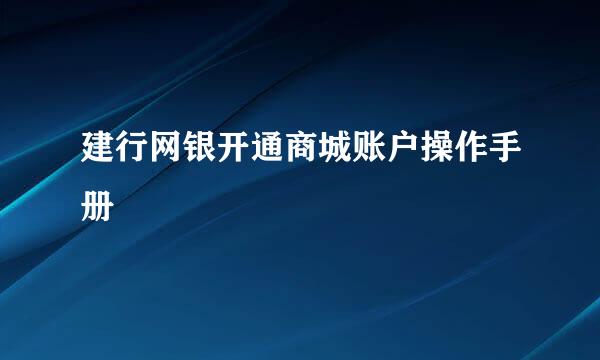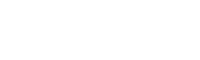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送给所有蜗牛宝宝的爸妈!
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:
“如影随形,母爱无言”这是写在刚刚上映的电影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海报上的话。所以,这部电影的最大亮点就是母爱,没有卖惨,没有大肆渲染自闭症,只是如同家常一样,讲述了母亲田桂芳和患有阿斯伯格症的儿子修直17年的陪伴和守护。对于修直,田桂芳的存在,如同一道光照亮了修直的世界,从此,他的眼中再没有黑暗……
作为一个典型自闭症孩子的母亲,几年前我曾有自己的工作,也常常活跃在本地的公益活动当中。后来生了自闭症宝宝,各地求医,总以为孩子能治好,结果花光了家底,卖掉了房子,也失去了工作,从此做全职陪读,陪伴孩子上特教学校已有多年。而现在,我和儿子倒常常成为“被公益”的对象。
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描述的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修直成长的故事,不像《喜禾》,没有过分突显人与人、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,也没有探讨孩子成长的复杂社会文化背景,在我看来,它更多地在描述母爱,只是将其置于“自闭症”这个话题当中。
因为观影前后,很多人都在从他们的角度谈论自闭症,有些人羡慕家中有这么一个“天才儿童”;有些抱怨自己的孩子只会玩手机,倒不如生一个修直这样的孩子;还有些“大咖”甚至开始谈论起自闭症的历史,抛出“根本不存在自闭症”这样的观点。所以在公共领域,有时候自闭症不是一个“事实”,甚至不是“现象”,而是一个“话题”,时冷时热,似乎谁都可以就自闭症“话题”发表观点,连一点专业门槛都不需要。这就是这次公益活动带给我的感受!观影结束后的公益沙龙上,几位自称组织者的大咖纷纷上台,轮番讲话惹人泪下,赢得阵阵掌声。我左右瞟了几眼,同为自闭症孩子母亲的观众倒是全程严肃,没鼓掌,也没落泪,包括我在内。而那些不明所以的观众跟随着“组织者”的引导不时地或笑,或哭,或沉思,或亢奋!
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?电影确实还不错,在“歌颂母爱”和“关怀特殊群体”两个主题的结合下,自然会感动一批人,“感化”一批人。对于我们这样的家长,可能看的不全是电影吧!
有多少片段曾是我们过去的缩影?
又有多少场景将会是我们未来面临的挑战?
可能,对于我这个资深自闭症孩子家长来说,不得不想的有点多,想得有点复杂?
与我同去观影的还有孩子的老师,跟他一路聊天,聚焦到这样一个争论:我们这次观影究竟是谈电影?谈公益?谈母爱?谈自闭症?还是谈别的什么?老师说,修直这个名字怎么感觉像是日本人的?不过从他的视角去看待母亲、看待自己的成长,这倒是一个稀缺的角度,导演跳出了以往那种特殊家庭惨惨戚戚的设定,跟《海洋天堂》不同,就凭这一点,会被认为其立意高超一些。正如北青报所说“跳出来看,这不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大成就么?假设导演有更多的预谋和追求,那么,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就不会是这样,需要公益爱心的呼吁和献唱。
特殊群体的生存质量反映一个社会的良心,关乎文明的尺度。但,大多数的“事实”并不能通过电影呈现出来,以至于带给很多人一种浪漫的、诗意的体验,就像上次“小朋友画廊”事件一样,仅仅是转瞬即逝的“话题”。很多人关注了一阵,朋友圈表态了一阵。但我们所经历的“真实”依然一如往常,我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这样一部电影发生质的改变。当然,我可能期待太多了。其实,电影的目的已经达到,我们家长也应该满足。
或许至少有一些人通过电影,片面地了解了这个群体,以至于在我们将来带孩子出入公共场所的时候,能够温和地对待我们;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,不会当他是熊孩子,不会排斥和歧视我们。
不过,就如同我在这群观众交谈当中发现的那样,我同样担心另一种情形:这部电影在带给普通观众以理解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同时,也带去了一些误解和刻板印象。我身边的家长不是说了嘛:没想到自闭症的孩子这么天才,我倒是希望孩子能像修直这样。这个想法换做我,同样适用,作为自闭症家长,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修直,毕竟他从小就有语言,说话还那么清楚,又有数学天赋……但这是我羡慕不来的。
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,一些公益常常止于感动,而爱心难出朋友圈。不出所料,很多人的朋友圈已经开始《我的影子在奔跑》了。朋友圈状态一条接一条。然后观影群里开始了一波关于自闭症的遐想,再过一天,群里安静地就像今晚的黑夜,再无声息。
因为在别人看来,他们讨论的是电影,是自闭症,是社会现象,是热点话题。但我们却是“当事人”,我们就是田桂芳们,虽然我们的孩子并不全是“修直”。
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,我们这些家长和这些家庭的经历就常常成为别人的“感动”素材,其实,我是一个感性的人,也常常被感动,但我很少说出来,我总觉得把感动说得太直白,甚至太过公开,总有点廉价,把原本的那种美好感觉稀释了。就像看到美好风景,不是沉醉其间去欣赏,而是急忙拿出手机拍照去记录一样。最终,我们和别人都是通过“照片”来窥见“真相”的。电影是艺术,而生活毕竟是生活。人们容易被感动,却从不轻易行动。
晚上,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文章,其中有这样的片段:赎罪券是一种宗教证券。在马丁·路德引发宗教改革运动的前夕,赎罪券被教会用来敛财。教皇的意思是,罪民们只要用钱敲击募捐箱,就能得到赎罪券,这样就可以免去上帝的惩罚,死后灵魂便能够上天堂;按照教条的说法,人人都是有罪的,所以在这段时期,几乎每天都有人去教会排队,用硬币兑换赎罪券。
在黑暗的中世纪,欧洲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灵魂的圣洁可以用金钱买到。也许很多现代人对此嗤之以鼻,但事实上这种现象在今天依然存在。
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,那些乡下的寡妇们常常会做一些令人奇怪的事情,例如去寺院里花钱捐一道门槛,意在让那道门槛代替自己被人践踏,为自己赎罪。这与中世纪欧洲的赎罪券如出一辙,同样是花钱买灵魂的圣洁的行为。
也许,“公益”在某些时候也承担这样的一种功能吧!在我们这个钢铁森林般的现代社会,亟需一些话题来呼唤人性的“温情”,留住“感动”,催人“流泪”。因为,并不是所有人难过时会流泪,开心时会大笑,人们需要一些“话题”,来找回我们原本的情绪,找回我们曾经失去的东西,类似修直那颗未经世俗社会浸染的赤子之心,那种孩童般的纯真和浪漫。
而找回这些需要多久,一部电影的时间!感动一阵,柔软一阵,足矣!然后继续在自己的生活“战场”上保持坚硬!我们始终在过自己的生活,与“他人”无关,就如同某人所说,“自闭”是我们的生活方式,对别人只是话题!